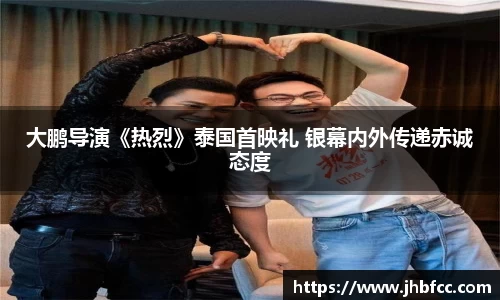閱讀量:1726 | 作者:超級管理員 | 發布時間:2025-09-03 10:54:54
2025年的暑期檔已經進入尾聲,電影市場表現出回暖的趨勢。
這其中,喜劇電影功不可沒。
《浪浪山小妖怪》《長安的荔枝》《戲臺》等影片在類型創新和文化表達上實現了喜劇電影多元化的呈現方式,滿足不同受眾、不同年齡觀眾的審美偏好。

但在這個夏天,也有一部分笑聲轉移到了小熒幕前。
今年6月,國內多檔脫口秀喜劇綜藝在流媒體平臺上線,即使我手機中沒有這些流媒體App,打開某音某書某號,這些脫口秀的切片、二創短視頻依然推到我手中的小熒幕上。
每時每刻,各大短視頻平臺上都有短劇網紅在不斷造梗、玩梗,以最快的速度博取笑聲,刷新觀眾的笑點密度。
這種段子化的搞笑類短視頻水平參差不齊,但也有其獨特的媒介優勢:能夠迅速捕捉社會熱點,即時制造梗點,快速傳播,并在幾秒鐘內幫助觀眾完成情緒的釋放。
在這些優勢面前,喜劇本身的跨媒介特征被不斷放大:它早已不再局限于劇場、熒屏或舞臺,而是通過短視頻、脫口秀、直播等渠道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碎片化娛樂中。
電影,作為過去幾十年喜劇的核心載體,既面臨沖擊,同時也憑借高口碑作品再次證明了自己在提供完整觀影體驗和情緒共鳴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媒介更迭,笑聲依舊
1984年春節,春晚第二次舉辦。導演黃一鶴找到演員陳佩斯和朱時茂,和他們商量出個語言類節目。
幾年前,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電影創作松了綁,陳佩斯與父親陳強共同主演的喜劇《瞧這一家子》,讓笑聲回到了影院。陳佩斯在片中飾演了有不少小缺點的年輕人嘉奇,影片中不少笑料都源自這個角色。
黃一鶴看過這部電影,也知道此后陳佩斯和搭檔朱時茂一直在琢磨創作幽默短劇,于是就干脆讓二人來到春晚舞臺上,為全國人民表演。
《吃面條》就這么誕生了。這種以戲劇排演為基礎,集合了各類表演藝術特點的新形式——小品,就這樣確立了下來。
小品時長短,場景簡單,依賴于喜劇演員在舞臺上對臺詞、包袱的精妙把控,在以電視為核心媒介的時代,這種喜劇形式立即成為普通觀眾獲取幽默和輕松情緒的主要途徑。
陳佩斯、趙本山、宋丹丹等舞臺、影視演員,更多的也以小品演員的身份被大家所熟知。
隨著公共電視臺的大量開辦與電視的普及,需要更多節目來填補內容時長,這種供求關系反映到喜劇創作上便誕生了情景喜劇。
1991年,鄭曉龍作為總策劃,找到王朔、馬未都、馮小剛等人,共同創作了第一部國產情景喜劇《編輯部的故事》,大約六億觀眾在熒屏前被逗的捧腹大笑。緊接著播出的《我愛我家》更是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不少經典笑料至今仍是中國觀眾口中的“祖傳梗”。
《我愛我家》
相比電視劇,情景喜劇不需要投入龐大的制作成本和拍攝周期,相比小品它的篇幅可以大幅延展,制作也更加精良,容易令觀眾形成長期的情感依附。不變的,是喜劇帶來的愉悅與笑聲,它滿足了人們對‘笑’這一精神慰藉的剛性需求。
情景喜劇和小品帶來的笑聲一直延續到00年代,隨著互聯網娛樂的興起,觀眾的笑聲開始從傳統的電視熒屏分流到網絡渠道。
觀眾獲取娛樂的方式從被動轉向主動,電視媒介的公共屬性逐漸瓦解。大眾的笑點也偏向個性化方向轉移,初代互聯網搞笑(惡搞)視頻的出現迎合并分流了年輕一代的笑聲。
相比其他傳統喜劇形式的衰落,世紀之交的喜劇電影正迎來自己的黃金時代。
相比電視熒屏上的火熱,喜劇電影的步伐要稍慢些。陳佩斯、趙本山等喜劇人也曾在90年前后參與電影創作,前者更是創辦大道影業想要在大銀幕上創出一番天地。
盡管陳佩斯嘔心瀝血拍攝了多部優秀的喜劇電影,但那時中國電影還未完成發行改革,瞞報票房的情況頻繁發生,最終公司破產,陳佩斯從銀幕回到了舞臺。
吃到時代紅利的,是馮小剛。1995年,時任紫禁城影業公司總經理的張和平見識到了檔期的潛力,將拍攝國內第一部賀歲片的任務交給了馮小剛。
“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它”
馮小剛拉著葛優、何冰、劉蓓等人很在1997年推出了《甲方乙方》,在90年代就獲得了3600萬票房,一舉奠定賀歲喜劇在廣大觀眾心中的文化地位,同時推動整個電影市場向商業化、娛樂化轉型。
隨著中國電影市場化改革,全國電影院線在新世紀重新煥發活力。銀幕數和影片數躍升,不僅帶動了“電影院”重新成為大眾文化生活的核心場所,也催生了“檔期”的概念,看電影逐漸成為日常消費娛樂的主流形態。
喜劇電影在這一過程中占據了天然的優勢,成為觀眾走進影院的首選類型,并在大眾娛樂版圖中確立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延續至今。
新媒介時代,喜劇告別大一統
互聯網進入3.0時代,媒介也完成新一輪的更迭,喜劇電影乃至整個電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環境。
近十年來,最具活力的“新興”喜劇形式是脫口秀。
它從最初的地下俱樂部、小劇場,逐漸被綜藝節目搬上流媒體平臺,諸如《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喜劇之王單口季》等節目卻熱度持續升高,通過切片、二創的短視頻在全網廣泛傳播,讓喜劇的笑點更快、更精準地觸達受眾,同時催生出付航、李雪琴、徐志勝等深受年輕人喜歡的脫口秀明星。
李雪琴也開始出演大銀幕作品
無論是脫口秀的表演形式還是傳播方式,都更貼近年輕人的日常生活。節奏更快,笑點直給,話題往往伴隨著職場問題、情感焦慮、女性困境等等,滿足了年輕觀眾對即時幽默和生活共鳴的需求。
而喜劇類短視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傳統情景喜劇在數字時代的“重生”。與脫口秀注重個人風格和即時互動不同,短視頻喜劇更加依賴情節設計與節奏把控,通常在幾十秒到幾分鐘內完成一個完整的笑點傳遞。
這種形式與傳統喜劇的包袱設計異曲同工,但更強調視覺化、節奏快、反饋即時。平臺算法進一步加速了內容分發,使熱門段子能夠在極短時間內觸達千萬觀眾。一位頭部喜劇短視頻博主向筆者透露,在流量巔峰時期,每條視頻全網的播放量都能達到千萬量級。
然而,正因為門檻低,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拍攝上傳短劇或搞笑段子,這也導致作品質量參差不齊。
創意缺乏打磨、互相抄襲、表演尷尬等問題普遍存在,形成“量多質低”的現象。過度依賴梗和熱點,也使得笑料生命周期極短,或圈層屬性濃厚,同樣一條短視頻,在不同年齡、興趣或地域的觀眾中產生的共鳴截然不同。
草根喜劇網紅的崛起雖然豐富了喜劇表現形式,但也凸顯了短視頻喜劇的局限性:它能在瞬間捕捉笑聲,卻難以提供深度人物弧光、復雜情緒體驗和長期觀影記憶。
這種即時性、碎片化的優勢與局限并存,也為喜劇電影面對觀眾分流時帶來了突破口。
暑期檔的喜劇,做對了什么?
還是回到電影。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夏天,喜劇電影證明了自己的韌性。幾部作品在創作和表達上都有各自的特色,也讓我們看到創作者在新時代怎么跟上潮流,努力把握各自受眾的笑聲與情感落點。
《浪浪山小妖怪》通過融合多種類型元素帶來驚喜。借助動畫形式,將喜劇與奇幻、冒險、動作等元素創造視聽體驗,通過奇幻世界的設定和角色反差制造笑料,這些手法令不同觀眾都能找到情緒共鳴點,在笑點與感動間找到屬于自己的宣泄出口。
相比之下,《長安的荔枝》在厚重的歷史背景下嵌入職場元素,觀眾在能輕松代入故事時保持愉悅的觀影體驗,共情小人物在宏大背景中自我價值的實現。喜劇元素在這里的功能更多體現在敘事氛圍的調節,而不是簡單的密集抖包袱博取觀眾笑聲。
《戲臺》則將傳統戲曲元素與現實題材巧妙融合,影片中每一個舞臺動作、臺詞節奏都經過精心推敲設計,并賦予文本豐富的文化內涵,幽默從嚴絲合縫的劇情邏輯中流淌出來,更體現一種含蓄而厚重的文化韻味和諷刺效果,而非單純的娛樂。“喜劇+”的復合類型模式是電影人目前給出的答案,加號的后面可以延展不同的類型、多樣的題材、復雜的情感層次。觀眾需要的不再是“兩個小時不停抖包袱”,而是能在類型故事與熟悉的文化語境中獲得愉悅感受,這種觀影體驗也正是對如今“短平快”笑點的一種對抗。盡管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其他喜劇媒介沖擊依然不容忽視,競爭環境的驟變,對喜劇電影創作者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復雜要求。喜劇電影不僅要提供笑聲,還必須提供短視頻和脫口秀無法替代的價值:完整的人物弧光,或是更復雜的故事和情感。這些差異性的體驗,才能讓喜劇電影在未來走得更遠,更好。
作者:日灼